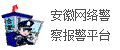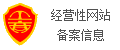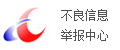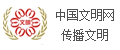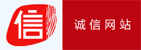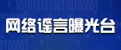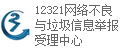當(dāng)前位置:網(wǎng)站首頁 / 文化·旅游
作家看太湖|連接湖海的愛戀
| 2024-12-04 11:23:47 編輯: 葉美霞 審核人:葉玲玲 閱讀次數(shù):19666 |
【編者按】
筆耕文海,尋跡太湖。日前,太湖縣融媒體中心精心策劃、組織、聯(lián)絡(luò)《中華文化》雜志社、安徽省報(bào)告文學(xué)家協(xié)會(huì)采風(fēng)團(tuán)走進(jìn)太湖,開展“書鄉(xiāng)村發(fā)展 看太美太湖”采風(fēng)活動(dòng)。采訪團(tuán)先后來到趙樸初文化公園、阿青牧場、田園大塘、花亭湖、五千年文博園、大石瓜蔞基地、安慶六白豬基地、花亭湖有機(jī)鳙魚基地等地,探訪綠色山水、紅色文化、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和社會(huì)變遷,通過筆觸展現(xiàn)太湖山水、名人、紅色文化之獨(dú)特魅力,以及在和美鄉(xiāng)村建設(shè)、鄉(xiāng)村旅游發(fā)展、“太商返鄉(xiāng)”創(chuàng)業(yè)、鄉(xiāng)村振興等方面取得的成效,講太湖故事,傳太湖聲音,展太湖形象,為助力太湖文旅事業(yè)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、推動(dòng)“大黃山”建設(shè)添上精彩一筆。現(xiàn)推出《作家看太湖》專欄,陸續(xù)推出采風(fēng)團(tuán)成員創(chuàng)作的精美作品,以饗讀者。
連接湖海的愛戀
朱其想/文
長江萬里此咽喉,吳楚分疆第一州。
——錢澄之,《送何別駕次公之皖》
萬里長江,是亞洲第一長河;自西往東,奔騰到海,浩浩蕩蕩,日夜不息。
其江上有“五虎”,自西往東:重慶、武漢、安慶、南京、上海。安慶在其中,在中段,是長江咽喉,是吳楚分疆之所。
沿途有無數(shù)支流猶如細(xì)流織錦,紛紛匯聚其下,共譜一曲壯闊的江河交響;皖河在此段匯入。皖山、皖河、古皖國,是安徽簡稱“皖”的由來。
還有散落的大湖,鑲嵌在長江這幅波瀾壯闊的畫卷上,宛若顆顆璀璨的明珠,在日光下熠熠生輝。太湖縣正是以“大湖”得名,境內(nèi)花亭湖,千重山色、萬頃波光,是大別山中第一湖。
大江東去,浪淘盡,千古風(fēng)流人物。長江邊上多豪杰,更是英雄的舞臺(tái)。中間安慶,更是風(fēng)流占盡;花亭湖邊,天下禪宗之根;道是鄉(xiāng)村之旅,卻成精神洗禮。
從太湖縣到上海灘
1920年元宵節(jié)剛過,一個(gè)年輕人從熙熙攘攘的上海吳淞口碼頭走了出來。第一次離開家鄉(xiāng),來到十里洋場;他充滿稚氣的臉上對(duì)于周圍還充滿了好奇。
這年他才13歲,確切是少年。
他從一個(gè)叫“太湖縣”的遙遠(yuǎn)地方過來,但太湖縣不在太湖邊,而在太湖的西面更西面;那個(gè)長江邊上的縣城,因?yàn)榇蠛啵?dāng)?shù)胤窖灾?ldquo;大”與“太”同音,而得名“太湖縣”。
及至后來少年去了江蘇的太湖,方知道即使太湖縣最大的湖也并沒有太湖大。果真山外有山而湖外有湖。
在上海,他見到了呱呱落地的表妹。他把可愛的小女孩抱在懷里,小女孩眨著眼睛與他對(duì)視,笑得可愛。
十幾年后,小女孩在文壇嶄露頭角。更多的人認(rèn)識(shí)到了這個(gè)才華橫溢的女孩,原名張瑛,后來叫張愛玲。
張愛玲的《金鎖記》被普遍認(rèn)為代表了她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。傅雷先生說這篇小說是“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”。
人們認(rèn)為《金鎖記》的原型正是李鴻章的長子李經(jīng)述一家。對(duì),藝術(shù)來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。
大清國最后的頂梁柱——李鴻章是張愛玲的外祖父,也是少年的曾姑爹。
少年沒有見過李鴻章;但是他每天兒時(shí)玩耍的屋檐下,掛著李鴻章為他家題寫的金字懸匾“四代翰林”。
他的祖屋被稱作“世太史第”,也是狀元府。
少年,名叫趙樸初。趙氏是安慶名門望族,從趙文楷到到趙樸初的爺爺,連續(xù)四代人“一狀元三進(jìn)士”,皆入翰林。翰墨飄香遠(yuǎn),詩書傳家久。
如今的太湖縣,以“樸初故里”為榮。盡管,他在那里僅僅度過了少年的一段時(shí)間,卻對(duì)他影響深遠(yuǎn)。趙樸初4歲從安慶回到祖居太湖縣寺前河生活,還常陪母親前往西風(fēng)禪寺。這西風(fēng)禪寺、西風(fēng)洞更是了不得的去處,是二祖慧可、五祖弘忍傳教的道場,冥冥中注定了趙樸初與佛教的緣分。
誰也沒想到,17年后的1937年8月13日,淞滬抗戰(zhàn)爆發(fā),難民如潮,躲入租界。
第二天,他在上海被報(bào)紙隆重登出來《趙樸初活菩薩》,成百上千的報(bào)童們沿街叫賣:“看報(bào)!看報(bào)!趙樸初菩薩再世,俠肝孤膽救難民!”
這年,趙樸初30歲。他并不是多大的官,也沒有多大的勢(shì);但是當(dāng)時(shí)民國政府與租界當(dāng)局管理無序,混亂中,唯有趙樸初挺身而出,手中高舉著紅十字旗,帶領(lǐng)著難民沿街祈求商家、學(xué)校、會(huì)所開放空地收容難民;他一路走、一路求、一路安置。
安置了之后,還有救濟(jì)、救治,趙樸初都成為了中堅(jiān)領(lǐng)導(dǎo)者之一。后來,趙樸初也當(dāng)過全國政協(xié)副主席等等許多更大的官職,但是他最輝煌的一天或許是高舉著紅十字旗沿街奔走的那一天,他的身后是數(shù)十萬上海難民。
那個(gè)畫面,我的腦海中也能勾勒出一幅名畫——類似于法蘭西的那幅《自由引導(dǎo)人民》。
那天,上海人民都感謝并記住了一位從太湖縣、花亭湖邊、西風(fēng)洞來的“活菩薩”。
從上海灘到太湖縣
君住長江中,我住長江尾。
如今從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到中游的安慶,高鐵只需要四個(gè)小時(shí)。要是中午出發(fā),便能趕上晚飯。
去太湖縣之前,我是有所期待的。我想從紛擾的城市到青山綠水間,尋找?guī)滋祀y得的清凈。
去看看山、看看水、看看名勝與古跡,去做幾天逍遙客。——我是這樣想的。
看得到山水美景,聽得到黃梅天籟,吃得到生態(tài)美食(比如六白豬與大魚頭),聞得到一樹一樹桂花香;若對(duì)禪宗歷史感興趣,要去爬西風(fēng)禪寺一級(jí)級(jí)的石階,趴每一塊石頭上感受得道高僧們的氣息。太湖縣,滿足了我對(duì)旅游的所有想象,大約是鄉(xiāng)村旅游的天花板了吧。
“大美”是對(duì)許多地方的贊揚(yáng),“太美”卻獨(dú)屬于太湖縣。走進(jìn)這片美麗而有靈氣的土地,才能發(fā)現(xiàn)他正孕育著巨大的改變。
滿地綠藤掛金蔞,從此致富不用愁。在大石鄉(xiāng),一位年輕帥氣的小伙站在手機(jī)屏幕前,通過直播帶貨銷售田中寶——瓜蔞籽;通過移動(dòng)互聯(lián)網(wǎng),直接將產(chǎn)品送入千家萬戶;既減少了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,又增加了品牌影響。這或許是后發(fā)優(yōu)勢(shì),也是彎道超車。
苔痕上階綠,草色入簾青。像羽毛一樣的羽蘚,喜歡長在水邊的匐燈蘚,喜歡長在石頭上的灰蘚......不起眼的苔蘚也在一位能人蔡長青的帶領(lǐng)下,成為致富一方百姓的產(chǎn)業(yè)。
他還在風(fēng)景優(yōu)美的泊湖邊建起了阿青農(nóng)場,能水上娛樂,可縱馬奔騰。夕陽西下,微風(fēng)拂過,湖邊的篝火晚會(huì)令人陶醉。
坐在湖邊,蔡長青講起了他的故事。年輕時(shí)候帶領(lǐng)了一客車的年輕人去城里搞建筑,一圈下來倒虧錢;背著好幾萬的巨額債務(wù)遠(yuǎn)赴東部打工,成了高管;又回到家鄉(xiāng)辦打火機(jī)廠,最多時(shí)候有兩百多員工;如今轉(zhuǎn)型一手抓苔蘚產(chǎn)業(yè),一手做鄉(xiāng)村旅游。
寥寥數(shù)語,道不盡創(chuàng)業(yè)艱辛。
在江塘鄉(xiāng),我還看到了宋柳林先生的“大手筆”,已經(jīng)在北京成功創(chuàng)業(yè)的他毅然回到家鄉(xiāng)建設(shè)了一個(gè)高標(biāo)準(zhǔn)的鄉(xiāng)村旅游綜合體——田園大塘,熱血滿腔,投資以億計(jì)。
回到家鄉(xiāng),回報(bào)桑梓。像宋柳林、蔡長青他們一樣回到太湖縣返鄉(xiāng)創(chuàng)業(yè)的人才越來越多了。
太湖縣的山山水水,包容了躲避滅佛之災(zāi)的二祖慧可,包容了挺進(jìn)大別山區(qū)的劉鄧大軍;更孕育出狀元府第,孕育出被周總理稱為“國寶”的趙樸老;還不斷涌現(xiàn)著中騰集團(tuán)李玉中、李斌,田園大塘宋柳林,阿青牧場蔡長青等創(chuàng)業(yè)創(chuàng)新路上的優(yōu)秀兒女。去親近山、去親近水、親近土地與空氣;想做逍遙客的我,卻沒成想到在這里找到了精神家園般的歸宿感。
無盡意
“生固欣然,死亦無憾。花落還開,水流不斷。我兮何有,誰歟安息。明月清風(fēng),不勞尋覓。”
來到太湖縣,當(dāng)然要拜訪趙樸初文化公園。趙樸老靈骨分葬三處,樹葬于斯地;安放杭州法華寺;海葬于上海。
出太湖而歸太湖,到上海而終上海;這是趙樸初與太湖縣、上海灘的緣分;更是萬里長江上,連接湖海的深深愛戀!
(作者:《中華文化》雜志編委、中國“中華酒”華東總代理)
上一條: 作家看太湖|太湖縣,心靈的詩意之旅
下一條: 作家看太湖|阿青牧場之歌